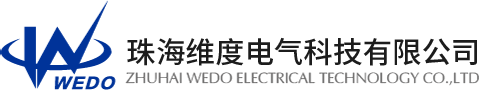eo圆桌 | “双碳”共识下,如何减碳成本更低
“发展的步伐可能确实要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用未来的成本降低来对冲当前的成本上涨压力。”国家电网财务部价格处处长吕栋表示,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共识下,对成本的容忍度有所上升,但是并不意味着成本可以放开上涨。
“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人将比现代人更富裕;现代人对于减排的投资是将现代人的财富转移给未来人。将穷人的财富向富人转移,会加剧代际社会不公平。”郭伯威说。
根据估算,中国2050年人均GDP将是2020年的2.3倍,而英、美两国则分别为1.6和1.5倍,中国经济增长更快,但消费者对高能源价格的承受力更低。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28.2%,英国为10.6%,美国为9.7%,以涨电价为例,英美国家中,电费在居民支出里所占的比重小于中国,因此其居民对涨价的承受能力相较中国也更高。
郭伯威指出,中国的代际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现阶段不适合过于激进的减排政策。实现碳中和要重点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矛盾以及代际社会公平性矛盾。
他进一步分析,经济总量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碳排放总量逐渐降低,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提升、经济集聚,是经济发展的附加红利,将降低减排成本。这意味着即使现在不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国的年均碳排放量也将达峰。
“要把更多减排任务留到后期。”郭伯威说,以2020年的物价水平来看,若能够保证代际公平,预计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减排总成本仅为8-16万亿人民币,约占2020年-2060年累计GDP总量的0.2%-0.4%。
中国价格协会能源和供水专委会秘书长、国中绿电(苏州)碳中和研究院院长侯守礼透露,在和一些园区企业交流过程中发现,大家都非常关心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增加多少成本、投资如何回收等问题。
侯守礼指出,要选择更加有利于实现碳减排的技术,引进新技术而增加的投资应通过节约电费等途径回收成本,以此解决投资收益的问题。
具体到电力行业,吕栋指出,电力系统正在从火电灵活性改造,发展分布式光伏,加快抽水蓄能建设,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等多个方面综合发力。目前来看,低成本措施穷尽后,也要推进一些高成本措施。减碳投资及成本会带来一定涨价压力,但远期来看,如果能够较大幅度降低光伏和储能成本,系统成本有望得到较好控制。
侯守礼建议,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过程当中,先期成本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这可以通过后期节能降耗减碳实现收益。“一方面,需求侧电价机制应进一步灵活起来,拉大价差,完善电价结构,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碳市场、用能权市场等要和电力市场实现联动,节能降耗和降低碳排放的收益应当显性化”。
全国碳市场已于7月16日正式开始交易。按照规划,电力行业是率先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业,后续将有更多行业被纳入市场。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张达研究估计认为,2020年到2030年,碳减排主要来自高效煤电机组对低效煤电机组发电量的替代。2030年后,随着基准线收紧,碳市场可以推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在煤电行业的部署。
逐步引入配额拍卖可以进一步促进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张达分析,在采用基于产出设计的碳市场中适度引入配额拍卖可使发电碳排放进一步降低。配合清晰的政策时间线,逐步引入部分配额拍卖可以在加速转型的同时,把供电成本上涨控制在适当的水平。
张达指出,拍卖产生的收入可考虑用于解决低收入群体能源价格的负担和碳市场分配公平性问题,一方面可考虑支持清洁取暖改造、煤电稳妥转型,另一方面可考虑用于投资低碳技术,促进更快脱碳。“我们粗略估计,如果拍卖比例为5%到10%,每年产生的收入是上百亿级的。”
在吕栋看来,碳市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配置各行业、各环节不同成本的减碳资源,谁的成本最低就优先减谁的碳,通过碳价鼓励使用最高效的方式减碳。
对于当前碳市场的金融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潘冬阳认为,过度金融化会衍生出碳经济泡沫,因此碳市场是否引入金融化问题亟待解决。
而对于欧盟拟启动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段茂盛指出,我国出口欧盟的中间产品中,80%的碳排放来自金属、化学和非金属矿物3个行业,这些行业均属于欧洲碳排放交易(EU ETS)的高泄露风险部门,一旦被纳入碳边境调节就会对出口产生巨大影响。
他建议,对于受欧盟CBAM影响的生产商,应在相关规则确定后尽快建立符合CBAM要求的内部监测体系。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指出,钢铁、化工、水泥等行业已高度市场化,当这些行业参与碳市场的时候,碳价可以向下游环节传导,也是在向全社会传导。但电力行业比较特殊,电力市场化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即便碳市场通过拍卖机制得出碳价,发电企业也只能是自己承担,并没有真正达到通过碳的社会定价来引导全社会降碳的目的。因此,碳市场和电力市场在中长期一定要耦合。
袁家海建议,现在现货市场中报价是边际燃料成本,未来应该是边际燃料成本加碳成本,但要注意对电力市场的价格机制产生的影响。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政指出,要打通两个市场的价格信号传导,确保碳市场与电力市场的协同运行。根据测算,当免费配额降到0、碳价上升到每吨200元左右的时候,煤电的度电碳减排履约成本将超过0.18元,接近现在煤电平均价格的一半,这也意味着碳市场将整体抬升化石能源发电机组的综合成本。
陈政建议,对于能源供应侧,要考虑价格疏导压力,适当延长发电行业燃煤机组等免费碳配额的周期,“电力几乎和所有生产生活相关,电价的上升将导致全社会用能成本上升”。
对于能源消费侧,陈政建议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考虑加快推进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能源消费侧“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进入碳市场,并收紧相关行业的碳配额,通过精准调控降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让碳减排效益最大化。
吕栋认为,电、碳市场的协同不是要把碳市场的成本全部转到电环节来,最后从电价疏导。电具有双重身份,一是自身减碳,另外是支持其他行业减碳,减碳的成本不应该都由电来承担。如果电力行业支持了其他行业减碳,应该把其他行业的这部分减碳收益用于支持电力行业减碳。
他指出,各行各业低碳转型还在起步过程中,工业领域相当一部分的用能需求还会向电转移,电力行业的碳达峰时间设置应略微滞后于其他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