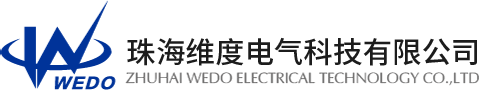碳中和时代,油企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嬗变
在“双碳”目标倒逼下,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主动适应全球能源行业新变化,研究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路线图,大力拓展天然气业务,寻找向电力转型新机遇,加快布局新能源业务,摆脱传统油气业务羁绊,向综合能源产品及服务商转型。
中国石油明确2021年将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注重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力争到2025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表示,要突出业务协同、专业化发展和产业链国内外一体化统筹,优化调整业务板块划分,构建油气和新能源、炼化销售和新材料、支持和服务、资本和金融四大业务板块(子集团),建立一整套紧密协同、内在联系、相互支撑的制度机制,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石化结合国家对能源化工行业发展战略需求,以碳中和为日标导向,加快推进氢能等先进能源和CCUS等深度脱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发展,制定低碳化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行业低碳转型,打造能源化工行业绿色低碳竞争力。中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公司将以“近零”排放为目标,推进化石能源洁净化、洁净能源规模化,生产过程低碳化,确保在国家碳达峰目标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
中国海油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发展新能源业务,稳妥有序推进海上风电业务。
作为国有大型能源央企,三大油石化企业在全球低碳转时代洪流下,从过去完全以油气为主业的企业,向综合性能源服务商嬗变。
“我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只是国家能源生产中具有很强专业性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其并存的还有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地热等多种专业性公司,主要从事一次能源开发,同时还有电力和氢能这样的二次能源公司为多种用户提供服务。”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表示。
吕建中认为,对大多数传统能源企业来说,一方面应把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点。以石油公司为例,应继续坚持大力发展天然气,特别是加强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进一步推动成品油质量升级等,促进环境问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提高终端能源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地热、生物质能、风能、光能等非化石能源产业化、规模化开发,提高新型清洁能源供应比重。
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大多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或中央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创新实力,可以在推动能源革命和转型升级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一方面,企业自身的技术转型要把技术研发和创新更多地转向清洁、低碳、高效利用能源领域,努力在关键性、前瞻性、颠覆性技术领域寻求突破。例如发展不同能源形式、能源和化工相互转化技术,发展减少能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技术,发展提升能源效率智慧能源技术,发展关键材料与装备制造技术等。
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提高能效、降低排放方面的新技术研发,及其在能源利用领域的普及推广例如可与大型能源用户共同研发节能减排技术、联合开展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天然气利用新领域的普及推广。例如可与大型能源用户共同研发节能减排技术,联合开展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天然气利用新技术等。引导企业把开发推广清洁低碳能源技术作为“双创”重点,为传统能源资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注入生机和活力。
石油央企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嬗变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依赖于技术突破,而且与发展环境、配套投入及互补性产品等在内的整个产业配套与支撑体系密切相关。如同生物群落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样,只有健康的产业生态系统才能促进产业发展与繁荣。重塑油气产业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吐故纳新,淘汰落后产能,推出新能源、新业态、新技术、新企业。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转型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实现油气被新能源跨越式替代。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尽管全球能源转型已从量变进入质变的全新历史阶段,但超越石油尚不现实。
2019年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4%和24%,新能源占15%,煤炭占27%;我国仍处于煤炭为主的时代,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能源消费的20%和7%,新能源占15%,煤炭占比超过50%。国外煤炭占比低,由主体油气向新能源转型潜力大;我国煤炭为主体,而油气占比低,且属稀缺性资源。能源消费结构特点及差异性决定了国内油气在能源转型中仍将是主要发展方向。
二是新能源存在行业壁垒且部分产业收益低,导致石油企业能源转型难度大。我国石油公司以经营油气为主,商业模式成熟,项目内部收益率一般需在10%以上。对于新能源领域,技术储备和商业模式尚未做好准备。
从产业转型潜力看,水能和核能属垄断性行业,市场较封闭且存在技术壁垒。风能和太阳能等长期由民企主导,市场竟争激烈,短期收益率低,仍属政策主导型产业。行业壁垒和盈利模式决定了石油企业向新能源转型存在较大阻力。▧来源:中国石油企业杂志